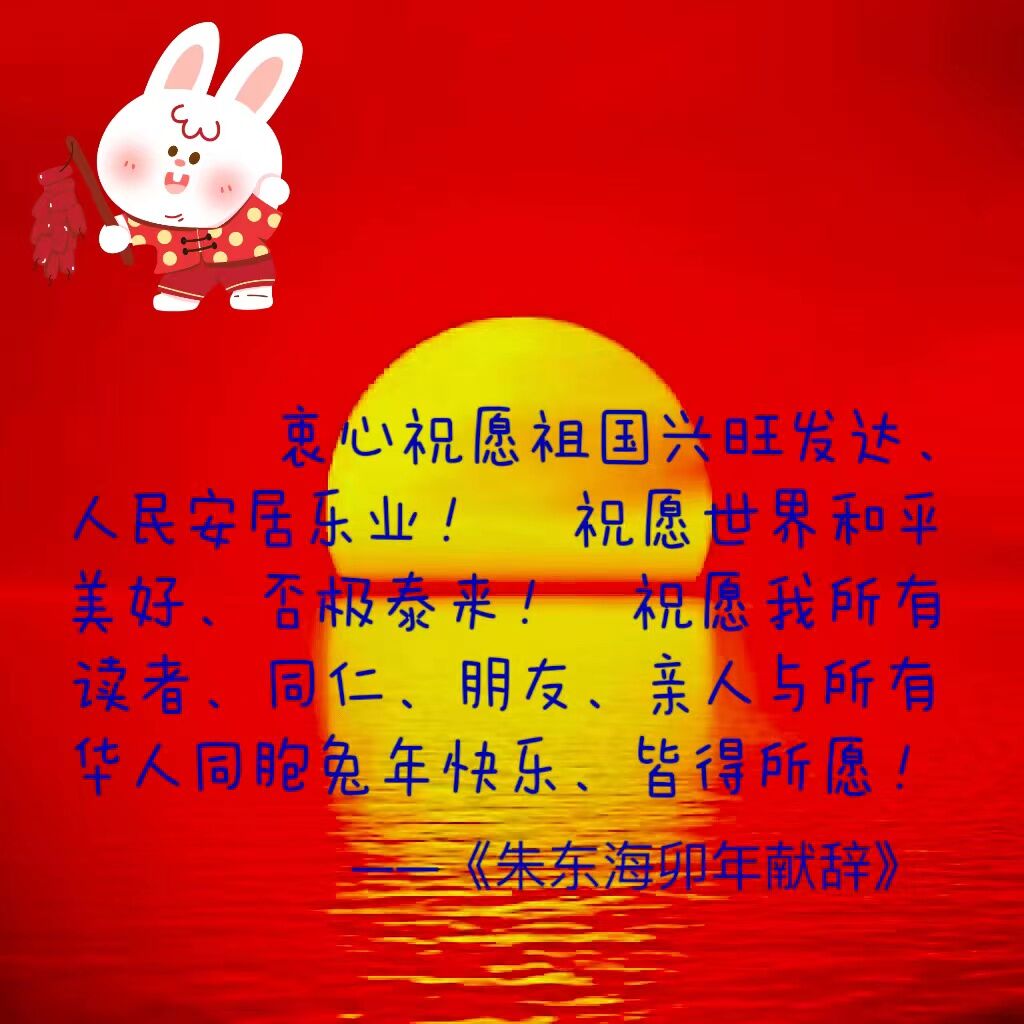爱国者杨振宁:“我是保守的革命者”-凯发k8网页登录

记者_陈祥 北京报道 摄影 _刘浚
杨振宁来了,89岁的他,无须旁人搀扶。他思维敏锐,虽然听力有所衰退。戴上助听器后,交流无大碍。一张娃娃脸,使他看上去年轻许多了。
服务员递上一杯咖啡,杨振宁利索地撕开糖包,加糖、搅拌,不见颤颤巍巍。时值午后两点,北京万圣醒客有点嘈杂,但随着讲话展开,四周人声逐渐稀疏。最终,全场只有杨振宁一人的声音,茶客们意识到这位老人正是杨振宁。
今年五月,由江才健撰写的《规范与对称之美—杨振宁传》正式出版。这是得到杨振宁个人首肯的一本传记。
传记追述了杨振宁的一生,但当日贯穿始末的采访话题,却绕不开杨振宁对中国模式不遗余力的赞赏。从中国传统到现代化政治治理,杨振宁无不一一表示佩服,并且认为压倒了他曾生活过的另一个国度—美国。
这当然不是杨振宁第一次如此显山露水地表达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,以及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。但正是这种情怀下的某些言论,让他近年来饱受批评。
对杨振宁提出诟病的,基本分为两大类:一是批评者者搬出以邓稼先、钱学森为代表的老科学家,指责杨振宁爱国晚矣,在美国赚得盆满钵满后才回国安享特殊待遇;另一边则批评他在各个公开场合的学术发言之外,不忘维护政权,替政府说话。
关于自己对中国的认识,杨振宁在文集《曙光集》中,提到一件往事。
1962年,杨振宁在日内瓦见父母,父亲告诉儿子,“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:从前不会做一根针,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。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,动辄死去几百万人,今天完全没有了。”母亲在一旁给父亲泼了冷水,“你不要专讲这些。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,排队站了三个钟头,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,有什么好?”
杨振宁认为父母的这两种观察并不矛盾,他将其归因于国家的诞生如同婴儿分娩,必会有阵痛。好与坏,都是中国模式成长中的一部分。
1971年,去国26年的杨振宁第一次回国探亲,回美国后对“文革”中的中国大加赞扬,尤其是四次访问中国后所作的谈话《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》,影响深远。多年以后,杨振宁对当年的言论失察作出过反省:
“我那时没有了解‘文革’的真相,我承认我是蹩脚的新闻记者。可是请注意我不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或心情去中国的。”
2004年,叶落归根的杨振宁在人民大会堂作演讲《归根的反思》时强调,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未能看到中国崛起的可能,是他无缘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韧性与中国共产党的韧性。
之后,风光无限的他,开始频繁公开发言,论调皆是强调在中外对比中,中国模式胜于西方。大谈中国学生的勤奋扎实,是杨振宁乐此不疲的话题之一。
很多人对此表示不以为然,在国际上享誉名声的数学家丘成桐,就指出,认为中国学生基础比美国学生扎实是自我麻醉。
杨振宁只字未提外界对自己争议的看法,更多时候,他沉浸在自己的话语氛围里。采访一结束,茶客们旋即围上来,拿着本子要他签名。签完第一批后,杨振宁挥挥手拒绝了第二批上前者。
杨振宁 “我是保守的革命者”
中国前沿科学前景乐观
南都周刊:国内外写你的传记有好些,为什么你独独认可这部?
杨振宁:比较实在,不浮华,少用形容词。这部书,跟中国过去出现的科学家的传记,形成一个极端的对比,江先生(江才健)在台湾做了很多年记者之后,写了一本《吴健雄传》,是按照西方写科学家传记的方法写的。他这样才认识我。后来他决定写这本传记,他的办法是遵循务实的原则,材料尽量要从实际出发,访问了很多人,我没统计,至少有上百人。花了相当长时间写出来,务求每句话都有根据,把我的方方面面都折射出来。
我认为这传记,比起绝大多数传记,不要说中国的,包括西方写得很好的传记,我觉得是毫不逊色的,置于国际标准下,也是非常好的。我说他是开了用中文写科学工作者的新纪元。
南都周刊:你对自己的传记有什么期待?
杨振宁:讲得不好听的话,中国方面发明了一个名词叫做传记文学。根据我的了解,很多作者认为既然是文学,可以渲染,渲染的程度,不同的作者写出来结果不一样,但都有渲染。这个观念我认为是不好,要如实道来。
南都周刊:就私人生活与学术研究两方面,对未来有什么打算?
杨振宁:我确实很幸运,从我的身体讲起来,到今天89岁了,还可以有很多种活动,多半89岁的人只能整天躺在床上了。学术活动,我还可以参与。比如过去两天在南开大学,他们组织了一个学术前沿研讨会,我参加了,见了好多年轻的朋友。好些是我不认识的人,他们作了演讲,对我有很大的好处,知道了年轻的一代热衷于作什么研究方向。莎士比亚说人到了年纪大时,没有牙齿没有眼睛,我远远超过这些。
我在1983年出了一本英文的选集,主要选了学术论文的三分之一,写一篇后记。至今快有30年了,30年里我陆续出了学术论文、科学史论文,还有一些别的文章。现在正在计划出“杨振宁论文选集与后记”续,正在做,希望在两年之内可以出版,也是英文的,这是我当前主要在做的工作。现在年纪大了,效率比较低,已经做了一年半,猜想至少还需要一年半。
南都周刊:刚才你说到与南开大学的年轻学子交流,觉得这一代人和你们当年西南联大一代人有什么差别和共通之处?
杨振宁:学术前沿改变很快。今天在全世界、在中国,物理学前沿的研究,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完全不一样。我总体感觉,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觉得中国的前沿科技发展很落后,甚至有人说中国政府每年几百亿地把钱撒到这上面,没出什么最重要的成果。
我认为这是对科技前沿发展的性质不够了解,科技前沿发展当然需要有钱撒上面,但绝对不是重要条件。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传统,传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建立起来,大家都知道剑桥的物理是非常成功的,但它是从19世纪就已经开始了。
所以从历史的眼光来看,在今天的中国,我听到四五十岁杰出物理学家作的报告,觉得中国今天达到的水准比起20年前,进步很多,不用说比起我做研究生时,进步更多。很显然的是,现在能够念研究院的人越来越多。改革开放后,中国的物理学、数学前沿非常非常落后,今天完全是不一样了。这两天我听到几个新的领域,都做了相当好的工作。从长远立场讲,我采取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。